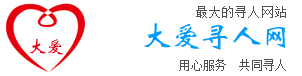卖孩子就像卖白菜 云南贩童黑帮之恶下
内忧外困的“王打拐”
和昆明刑警赵建国一样,人称“王打拐”的昭通著名打拐警察王一民用“内忧外困”来描述他近来的状况。自1998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进行专项的打拐工作,每次打击都或多或少有所斩获。
“但问题在于,这些打击都是临时性的,因此导致打拐工作的随意性很大。”王一民说,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云南贩卖幼童形势之所以特别严重,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就由于较长时间没有进行这样的打击。
王一民提出疑问,2004年“百日会战”打拐大行动,固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是不是有“一阵风”的嫌疑?
在打拐机构的设置上看,一般县级以上的政府有一个打拐领导办公室,设在公安局,但大多数打拐办一般情况下有牌无人,在需要打击的时候才临时从各部门抽调几个人。王说,有可能每次抽调的人都不一样,这样的打击没有连续性,也不利于案件的侦破(有些案件办了一半,人员换了,又得重新追查)。
而且,云南警方内部掌握的数据说,贩卖幼童案的立案率不到25%,具体到昭通等地区,立案率甚至更低。
王一民说,在一些地方,本来一些案件完全可以向省公安厅申请督办,以求获得更大的破获机会,但由于某些领导的认识不足以及诸多“其他考虑”,往往被压下来作一般案件处理,以至至今尚未告破。
所以,出现贩卖幼童案久打不绝,民间称之“打拐打拐,越打越拐”的情况(拐:土话,糟糕的意思)。
王一民的“内忧”还体现在经费的紧张上。
打拐耗资巨大,根据核算,解救一个幼童平均要花费3万至5万元,而现实是,警方在本身经费不足的前提下,很难有专项的打拐经费。
昆明市公安局近期一份报告中说,“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下”,市局每年可以从财政预算中划拨20万元作为打拐经费,这20万元“和承担的任务所需经费相比,存在较大缺口”。nbsp;
而王一民日常的打拐是没有经费的,只在专项打击的时候才能打报告去要一点,“像挤牙膏一样”。
王一民害怕出差,因为每次即便“连脚指头都扳着计算”还要贴钱:到省外,每天包括住宿、车船、吃饭在内总共只能报销58元,连出租车都不敢打。王最窘迫的一次经历是2002年冬天的一次行动,他和5名同事赴福建执行任务,下火车后在瓢泼大雨中找了4个钟头才找到一家廉价的小旅馆。窘迫中王想出了一个节约的好办法:尽量在晚上乘车,既赶了时间又节省了住宿费。但这仍然不够,需要开支的实在太多。王说,他们局凡是打拐的警察或多或少都欠了单位的钱,而他本人,目前的欠账高达数万元。
幼童被解救回来后的善后问题又是一件棘手的事。帮幼童们找到他们的生身父母,对办案警察来说,似乎顺理成章、义不容辞,但这严格说起来并非警方的业务范畴,何况做这些事费时费力,还得花费一笔包括DNA亲子鉴定、生活费等不小的开支。
王一民所在的昭通,没有儿童福利院,因此不能像昆明同行那样让福利院分担一部分善后工作,那些找不到父母或者父母不愿领回家的幼童——父母将自己孩子卖掉的,一般找回来后不愿领回家——王一民和他的同事们还得给他们找个收养人,但这样也存在风险,保不准收养的人再次将幼童卖掉,那前面的打拐解救就付诸东流了。
“王打拐”们还时时遇到一些法律上的两难处境。那些自己生孩子卖的人从法理上来讲也算拐卖,按理也应该抓起来,可是他们的子女怎么办?在理论界,关于自生自卖算不算拐卖、犯罪颇有一些争议,这客观上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另外,那些买主算不算违法犯罪?要不要打击?法律没有作出明文规定。
还有,如果一个地方犯罪太普遍了,打击起来也很头痛,像龙乜村那样,一个村75%以上的成年人参与贩卖,于理于法应该全部抓起来,但整个村也就空了,他们的儿女谁来抚养?看守所、监狱能容纳得下这么多罪犯吗?
打拐多年,王一民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威胁:有人曾放言,决不放过他和他的家人。而另一方面,许多被拐幼童的父母,也因为警方打击不力或者对他本人的误解,不断地控告他。
这是王一民的“外困”。
民政介入反拐善后
因为警方在善后问题上的诸多难处,去年“百日会战”期间,根据昆明市政府的要求,昆明市民政局管辖下的儿童福利院正式介入反拐的善后工作——暂时收留、代养那些被解救回来尚未找到父母的儿童。
在此之前的决策过程曾出现过波折,民政局和福利院表示,不愿接收那些被解救回来的儿童。
昆明市民政局一位姓张的处长说,首先,吸收打拐解救回来的儿童不是民政的长期职责,按照法律规定,儿童福利院的收养对象是弃婴和孤儿;其二,还有个数量问题,如果打拐解救回来的儿童很多,突然来一大批,儿童福利院也不能承受——福利院目前收养的儿童已达600多个,已到福利院所能承受的极限,另外,福利院的员工只有60多个,也没有过多的人手来照顾解救回来的儿童;其三,经费问题,这些孩子的生活、医疗以及其他费用,谁来负担?其四,风险问题,这些解救回来的儿童若发生死亡,责任谁负?另外,庞大的认领工作,也将对福利院的正常工作造成干扰。
福利院则担心:这些儿童在被拐卖期间生存条件恶劣,解救途中又长期乘坐火车,说不定身带恶疾,带回福利院有交叉传染的可能;一些年龄稍大的孩子,在经受了生死分离的考验后,有心理疾病,除了本身很难照看外,还会影响到福利院原有的儿童。
在昆明市政府“以大局为重”的态度下,且昆明市政府允诺以纳入社会低保的方式解决这些孩子的经费,民政、福利院答应和公安合作,但是问题又来了。
民政要求警方移交孩子的监护权,因为监护权移交后,那些孩子才能落户办理身份证,才能享受到低保待遇;另外,监护权移交后,福利院可以为这些孩子找到认养人,给他们一个新的家庭;一旦发生死亡,也不会出现说不清楚的麻烦——民政还附带一个条件,移交监护权的孩子年龄应该小一点,这样容易找到认养人。
但警方拒绝移交监护权。昆明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说,监护权一旦移交,孩子的父母万一找到了肯定不干,公安局说不定得吃官司。
经过争执,最后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警方将孩子交给福利院代管,为期三个月——警方找到孩子父母的时间大约需一至三个月。这期间的一切费用由警方承担。
此后,一共有两批共33名被解救回来的儿童,经警方送医院体检交给了福利院,福利院将这批儿童交由市郊一些人家寄养,由福利院每月支付一个儿童400元的寄养费,买衣物玩具教育看病等费用另外开支,福利院认为这些费用理所当然应当由警方开支,目前正在追讨之中。
福利院院长赵锦云女士认为警方的某些做法还有待完善。她建议警方可以事先做好那些失踪孩子父母的DNA鉴定数据库,一旦孩子找到,就可以迅速对证,不会像现在这样折腾,“打拐是好事,但是怎么打?我认为应该以人为本,以人的出发点和归宿来打”。
据了解,目前已有6名儿童被父母认领回家,其余仍由福利院代管。其中的许多未尽事宜,有待解决。
赵女士说,从内心深处,她希望警方能尽最大努力找到孩子们的亲生父母,否则,宁愿接受现实,让那些已经熟悉新环境的孩子留在“买主”的家里,毕竟孩子最后的归宿是家庭,“从孩子们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他们对养父母(买主)非常的依恋”,她甚至提出疑问,有必要再给这些年龄渐大的孩子重新找一个家吗——当然这未必合法。
“是改变战略重点的时候了。”云南省妇联权益部部长贺平说,贩卖幼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从各种渠道、各个角度和层次来解决。
2004年7月6日至8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
机构间湄公河次区域打击拐卖人口项目及英国救助儿童会,在昆明举办五省预防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经验交流会,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公认,我国目前的打拐工作中存在许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缺乏一个清晰而完整的“长久之计”,反拐工作的战略重点出现偏颇:长期以来,反拐主要停留在事后的打击上,“一提到反拐,只知一味剿、剿、剿”,政府官员有一个错误的思维:宁愿花更多的冤枉钱来解决问题,也不愿把问题扼杀在萌芽之中。
专家们认为,这导致警方承担了过多的职责,用云南省公安厅的话来说,警方目前负重太过、苦不堪言,出现了公安一家单打独斗、公安内部又是刑侦一家唱“独角戏”的被动局面……”
警方苦不堪言到了什么程度?
在昆明,“百日会战”期间,迫于形势,警方给各派出所下达了一道死命令:辖区内再发生孩子失踪和被拐卖的案件,负责辖区的片警将一律下岗,所长免职;同时,实施案情“回报制度”,已经立案的案件,负责案件侦破的警察应该每天向失踪孩子的家长报告案情进展,如果群众提出意见,负责案件的警察也将受到下岗处分——昆明市公安局一位官员说,局领导也自知此举太过,“但没办法,来自上面和各方的压力太大,而且局领导也希望改变过去那种局面”。
此举在昆明民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一些了解警方难处的被拐孩子家长说,“我们很感激警方所作的姿态,但警察也是人……这样做我们以后也不好来报案了”。
贺平说,单纯打拐,结果却越打越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治病之道,“我觉得政府更应该像一个优秀的中医,整体看待病人,标本兼治”。
实际上,云南省公安厅自1999年始已对反拐及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反思,得出结论:反拐不是一个单一的打击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是一个维护儿童权利、涉及到“人权”维护的问题。警方因此萌发了改变现状的想法,当时云南公安厅刑侦总队高层已提出全社会参与、整体联动,变单一打击为预防为主、打击为辅的方向,并酝酿在社区建立预防拐卖的社会长效机制。
警方的观点跟一些社会群体和国际儿童权益组织不谋而合,早在多年前,他们就密切关注云南贩卖幼童的形势发展并着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1999年底,云南省公安厅与代表社会群众团体的省妇联、代表国际民间组织力量的英国救助儿童会联合在文山州广南县龙乜村启动了“多部门合作社区预防妇女儿童被拐卖”项目,尝试在农村社区将包括上至多个政府职能部门、下至每个村民的社会资源调动、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实现防止拐卖。
这一模式的具体实施是,组织成立一个多部门项目合作的机构网络,网络中的各部门都有一定的职责范围,公安负责治安管理,妇联负责唤醒妇女的权利意识以及维护孩子的权利意识,综合治理办公室则负责协调上层领导部门诸如政法委等等,将领导力量纳入网络;林业、农业负责在项目实施地的经济发展(拐卖发生的根源在于贫穷),以及争取政策和资源———龙乜在过去是又穷又不受重视,许多扶持政策得不到。
项目还对各级别的部门以及社区的居民特别是村民们进行了培训,让他们明白各自的社会责任,以及自身的权利。因此,项目是在一方面加强权力部门的资源整合,一方面高度发掘村民自治的潜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赵捷说,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项目,实施4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那些过去的人贩子、罪犯、违法者,现在转而成了妇女儿童权益的维护者。
这个基于中国国情和地区实际而设计、运作的、被称为龙乜模式的项目,因为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在五省会议上被介绍给国内外132名专家、学者,目前已成为国内外极好的行动性研究案例。
英国儿童救助会项目经理黄金霞透露,目前他们和云南省妇联、公安厅正致力于龙乜模式的完善,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政府对反拐工作的重视及全局性考虑——理想的状况是,在省综合治理办公室设置一个反拐领导小组作为长效机构,把反拐纳入社会治安的常规工作,纳入各级官员的考核指标,以根本改变过去“运动式”的局面。
在贺平摊开的地图上,云南省的38个村标上了小红旗:省妇联已联合云南省综合治理办公室、公安厅、司法厅等门,并向云南省政府提出专项申请,筹集资金,拟在这些拐卖重灾区推广龙乜模式。
当然,这一模式的可复制性和长期有效性,还需实际效果的检验。
“一定看好自己的小孩啊,不然走丢了会后悔死的。”李启方回忆说。
李启方当胸举着个自制的大牌子,上面贴着一张4岁儿子李升的照片,旁边是用黑笔写的寻人启事。在他身旁,是40多个同样装扮的父母,大多眼含泪水,手挽手站在一起。碰到有过来询问的,就给对方看自己孩子的照片。
他们都是外地来昆的打工者,都在昆明丢了小孩,为了找回自己的“心头肉”,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呼吁社会的关注。
这样的自助团体被称为“寻子联盟”,共有近400个失子家庭参与其中,分布在广东、福建、贵州、湖北、河南、天津、云南等地。
生计,与孩子
这些丢失孩子的打工者,以摆小百货、卖衣服、卖鸡鸭等为职业的小生意人居多,他们通常住在人员混杂、治安较差的“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一边为生计奔波,一边要照看孩子。
他们的孩子也就成为了人贩子拐卖的首选目标。李启方所住的昆明市北郊官渡区,作为昆明外来打工者聚集处,同时也是儿童丢失最多的地区。近几年,该地区已经丢失儿童200多名,占到昆明被拐儿童总数的70%,绝大多数为外地打工者的孩子。
然而,这些外来工家庭有时候感到孤立无援。许多家长踏上了依靠自己力量寻找失踪孩子的漫漫长路,尽管这路走得那样艰辛。
湖南怀化的戴先生,为找到自己5岁的儿子,半年来跑了十多个省市,从云南出发,经两广、福建,一路北上直到上海,“南边半个中国都走遍了”。前后发了500万份寻人启事,并给全国2786个县级公安局发了求助书,花了30多万元,“小孩看了很多,但都不是我的”。
类似的情形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失踪孩子的家庭,为找孩子这些家长“像个无头苍蝇,到处闯,可一点线索也没有”。许多人为找孩子花光了自己的“全部家底”。
“人多力量大”
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成规模的“寻子联盟”主要有三处:云南昆明的“寻子联盟”集合了178个失踪孩子的家庭,广东东莞的“寻子联盟”组织起87个失踪孩子的家庭,河南郑州的“寻子联盟”有10个失踪孩子的家庭参与。最初一般只有几个家长,后来人越来越多,逐渐发展壮大。他们在一起,互相提供各自掌握的消息,彼此安慰。
林舜明在丢孩子后,“天天买报纸,就看看哪里有丢孩子的”。有一次,报上称一个市场近两年陆续丢了七八个小孩。他们几人就去市场周围四处打听,看到墙上贴的一张寻人启事,就联系上了其他寻子者。
这次行动,使得东莞的“寻子联盟”又多了六家新成员。为了联系更多的家庭,他们甚至还实行了“分片包干制”,选出住在不同地方的几位代表,各自负责自己所在的区域,有的还通过报纸、网络,广泛联络外省的失子家庭。到年底,东莞“寻子联盟”就联系到全国各地近百个丢失孩子的家庭。
而东莞“寻子联盟”负责人林舜明同昆明“寻子联盟”负责人李启方的相遇更富戏剧性:2004年7月22日,李启方被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请去做了一期节目,在节目中李启方讲了自己的遭遇以及昆明“寻子联盟”的一些情况,并播放了当地电视台拍摄的他们在东风广场上的镜头。
“也就一两秒钟吧,我就看到了一个家长牌子上黑笔写着的电话号码”,林舜明回忆当时看电视的情景,他今天还能记得这个0871-4591×××的电话。
按照电话打过去,从那要了李启方的联系方式,“我们两家就联系上了”。
后来,林舜明还带李启方到自己家乡找过孩子,他讲了那次的经历:
“我家乡潮汕那边,‘传宗接代’的想法很流行。有些人家连续生了几个女的就是没男孩,会托人买个男孩子传递香火。这样一来,买孩子的就很多。
“我知道有个8岁男孩,卖到我家乡有4年了,现在还记得他家附近有火车经过,他爸爸是个卖猪肉的。
我把消息提供给大家,李启方告诉我,他家就住在火车站不远,基本情况差不多,就打算过来看看。当时我还有顾虑,但是一想,都是丢小孩的,能帮上的还要帮。他在学校门口等了一天,最后没等到。”
孩子虽然最后没有找到,但毕竟增加了人们的信心,“你能保证下一个就不是自己的?”一位湖北的家长这样说道。联盟里的家庭,更多的时候是在彼此鼓励,彼此温暖。“现在,在外面看见别人一家三口,心里就堵的慌”,深圳的一位家长说,“我们这些不幸人聚在一起,感觉要舒服点。”
他们经常碰头。地点近的,两三天碰一次面;远点的,就隔十天八天去一下。路上打车,都是“抢着付钱”。到谁家,正赶上吃饭,“没有菜,就一锅粥,也要给盛一碗”。电话互相打,“大家聊一聊,可能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可是心情会舒畅些。”
林舜明说的更明白,“同病相怜”。
他们还会有一些集体行动,督促政府相关部门,呼吁社会关注。如2004年11月27日,郑州“寻子联盟”的10名家长在郑州市二七广场打出横幅,上书“10名被拐孩子父母用心良苦,20万重金酬谢好心人”;2004年12月20日,东莞“寻子联盟”的30余位家长一同进京,向公安部、全国妇联反映情况。
“毛主席说的对嘛,人多力量大。”贾少令很认真地对记者说。
“一定还活着,一直找下去”
家长们的不懈努力似乎起到了一些作用。丢失孩子严重的地区的政府对这个问题开始给予重视,采取了一些专项行动。拐卖孩子的“重灾区”——云南昆明的警方在去年下半年展开了一项百日打拐行动,要求在百日内投入百名干警花费百万元解救百名儿童。郑州市则于2004年12月29日,召开“打拐”工作会议,郑州警方向全市公布10名儿童信息,警方刑事技术部门在原先失踪人员DNA数据库中增加失踪儿童数据库。并特批20万作为专项经费。随着警方打拐力度的加强,一些被拐儿童也陆续被解救回来,其中有一些是“寻子联盟”中的失踪孩子。
2005年1月5日,被拐两年的5岁儿童郑帅权成为郑州“寻子联盟”中找到的第一个孩子。2005年1月7日东莞“寻子联盟”负责人林舜明的孩子林杰涛也被当地警方在江西找到。
“我还是那个观点,你一个人,再多钱都没用,把人凑起来才有力量。”林舜明如今谈起自己组织起来的这个“寻子联盟”,很自信。他觉得自己能找回孩子,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公安局重视了,再加上自己提供的有用的线索,“案子不就破了”?如果没有人主动搞这些事情,比如联系失子家庭,接受媒体采访,去北京反映情况,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他表示其他的家长“还得这么做”,还得继续团结起来。
林舜明在送别记者时,满脸是笑,他说自己这半年来从没有笑得这么开心,“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早日找得到,大家都开心”。
然而,“寻子联盟”近300个失子家庭中真正找到孩子的还是少数,大多数的家长还在煎熬与等待中苦苦度日。
唐建勋的儿子唐小虎,2000年11月2日被人拐走,4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寻找,从未想过放弃,“只要国家公安机关出力的话,应该还是有一点希望的”。
过去喜欢逗孩子玩的老唐,现在最怕见别人家的孩子,“看了就伤心,就想自己的儿子,想我的小虎。”
说到这,这个一直很倔强的男人,眼里都是泪。咬了咬嘴唇,半天才说出一句来:“我就想,一定还活着,我就一直去找!” 作者: 曹勇马晖 2005年01月20日10:05 南方周末
和昆明刑警赵建国一样,人称“王打拐”的昭通著名打拐警察王一民用“内忧外困”来描述他近来的状况。自1998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进行专项的打拐工作,每次打击都或多或少有所斩获。
“但问题在于,这些打击都是临时性的,因此导致打拐工作的随意性很大。”王一民说,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云南贩卖幼童形势之所以特别严重,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就由于较长时间没有进行这样的打击。
王一民提出疑问,2004年“百日会战”打拐大行动,固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是不是有“一阵风”的嫌疑?
在打拐机构的设置上看,一般县级以上的政府有一个打拐领导办公室,设在公安局,但大多数打拐办一般情况下有牌无人,在需要打击的时候才临时从各部门抽调几个人。王说,有可能每次抽调的人都不一样,这样的打击没有连续性,也不利于案件的侦破(有些案件办了一半,人员换了,又得重新追查)。
而且,云南警方内部掌握的数据说,贩卖幼童案的立案率不到25%,具体到昭通等地区,立案率甚至更低。
王一民说,在一些地方,本来一些案件完全可以向省公安厅申请督办,以求获得更大的破获机会,但由于某些领导的认识不足以及诸多“其他考虑”,往往被压下来作一般案件处理,以至至今尚未告破。
所以,出现贩卖幼童案久打不绝,民间称之“打拐打拐,越打越拐”的情况(拐:土话,糟糕的意思)。
王一民的“内忧”还体现在经费的紧张上。
打拐耗资巨大,根据核算,解救一个幼童平均要花费3万至5万元,而现实是,警方在本身经费不足的前提下,很难有专项的打拐经费。
昆明市公安局近期一份报告中说,“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下”,市局每年可以从财政预算中划拨20万元作为打拐经费,这20万元“和承担的任务所需经费相比,存在较大缺口”。nbsp;
而王一民日常的打拐是没有经费的,只在专项打击的时候才能打报告去要一点,“像挤牙膏一样”。
王一民害怕出差,因为每次即便“连脚指头都扳着计算”还要贴钱:到省外,每天包括住宿、车船、吃饭在内总共只能报销58元,连出租车都不敢打。王最窘迫的一次经历是2002年冬天的一次行动,他和5名同事赴福建执行任务,下火车后在瓢泼大雨中找了4个钟头才找到一家廉价的小旅馆。窘迫中王想出了一个节约的好办法:尽量在晚上乘车,既赶了时间又节省了住宿费。但这仍然不够,需要开支的实在太多。王说,他们局凡是打拐的警察或多或少都欠了单位的钱,而他本人,目前的欠账高达数万元。
幼童被解救回来后的善后问题又是一件棘手的事。帮幼童们找到他们的生身父母,对办案警察来说,似乎顺理成章、义不容辞,但这严格说起来并非警方的业务范畴,何况做这些事费时费力,还得花费一笔包括DNA亲子鉴定、生活费等不小的开支。
王一民所在的昭通,没有儿童福利院,因此不能像昆明同行那样让福利院分担一部分善后工作,那些找不到父母或者父母不愿领回家的幼童——父母将自己孩子卖掉的,一般找回来后不愿领回家——王一民和他的同事们还得给他们找个收养人,但这样也存在风险,保不准收养的人再次将幼童卖掉,那前面的打拐解救就付诸东流了。
“王打拐”们还时时遇到一些法律上的两难处境。那些自己生孩子卖的人从法理上来讲也算拐卖,按理也应该抓起来,可是他们的子女怎么办?在理论界,关于自生自卖算不算拐卖、犯罪颇有一些争议,这客观上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另外,那些买主算不算违法犯罪?要不要打击?法律没有作出明文规定。
还有,如果一个地方犯罪太普遍了,打击起来也很头痛,像龙乜村那样,一个村75%以上的成年人参与贩卖,于理于法应该全部抓起来,但整个村也就空了,他们的儿女谁来抚养?看守所、监狱能容纳得下这么多罪犯吗?
打拐多年,王一民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威胁:有人曾放言,决不放过他和他的家人。而另一方面,许多被拐幼童的父母,也因为警方打击不力或者对他本人的误解,不断地控告他。
这是王一民的“外困”。
民政介入反拐善后
因为警方在善后问题上的诸多难处,去年“百日会战”期间,根据昆明市政府的要求,昆明市民政局管辖下的儿童福利院正式介入反拐的善后工作——暂时收留、代养那些被解救回来尚未找到父母的儿童。
在此之前的决策过程曾出现过波折,民政局和福利院表示,不愿接收那些被解救回来的儿童。
昆明市民政局一位姓张的处长说,首先,吸收打拐解救回来的儿童不是民政的长期职责,按照法律规定,儿童福利院的收养对象是弃婴和孤儿;其二,还有个数量问题,如果打拐解救回来的儿童很多,突然来一大批,儿童福利院也不能承受——福利院目前收养的儿童已达600多个,已到福利院所能承受的极限,另外,福利院的员工只有60多个,也没有过多的人手来照顾解救回来的儿童;其三,经费问题,这些孩子的生活、医疗以及其他费用,谁来负担?其四,风险问题,这些解救回来的儿童若发生死亡,责任谁负?另外,庞大的认领工作,也将对福利院的正常工作造成干扰。
福利院则担心:这些儿童在被拐卖期间生存条件恶劣,解救途中又长期乘坐火车,说不定身带恶疾,带回福利院有交叉传染的可能;一些年龄稍大的孩子,在经受了生死分离的考验后,有心理疾病,除了本身很难照看外,还会影响到福利院原有的儿童。
在昆明市政府“以大局为重”的态度下,且昆明市政府允诺以纳入社会低保的方式解决这些孩子的经费,民政、福利院答应和公安合作,但是问题又来了。
民政要求警方移交孩子的监护权,因为监护权移交后,那些孩子才能落户办理身份证,才能享受到低保待遇;另外,监护权移交后,福利院可以为这些孩子找到认养人,给他们一个新的家庭;一旦发生死亡,也不会出现说不清楚的麻烦——民政还附带一个条件,移交监护权的孩子年龄应该小一点,这样容易找到认养人。
但警方拒绝移交监护权。昆明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说,监护权一旦移交,孩子的父母万一找到了肯定不干,公安局说不定得吃官司。
经过争执,最后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警方将孩子交给福利院代管,为期三个月——警方找到孩子父母的时间大约需一至三个月。这期间的一切费用由警方承担。
此后,一共有两批共33名被解救回来的儿童,经警方送医院体检交给了福利院,福利院将这批儿童交由市郊一些人家寄养,由福利院每月支付一个儿童400元的寄养费,买衣物玩具教育看病等费用另外开支,福利院认为这些费用理所当然应当由警方开支,目前正在追讨之中。
福利院院长赵锦云女士认为警方的某些做法还有待完善。她建议警方可以事先做好那些失踪孩子父母的DNA鉴定数据库,一旦孩子找到,就可以迅速对证,不会像现在这样折腾,“打拐是好事,但是怎么打?我认为应该以人为本,以人的出发点和归宿来打”。
据了解,目前已有6名儿童被父母认领回家,其余仍由福利院代管。其中的许多未尽事宜,有待解决。
赵女士说,从内心深处,她希望警方能尽最大努力找到孩子们的亲生父母,否则,宁愿接受现实,让那些已经熟悉新环境的孩子留在“买主”的家里,毕竟孩子最后的归宿是家庭,“从孩子们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他们对养父母(买主)非常的依恋”,她甚至提出疑问,有必要再给这些年龄渐大的孩子重新找一个家吗——当然这未必合法。
“是改变战略重点的时候了。”云南省妇联权益部部长贺平说,贩卖幼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从各种渠道、各个角度和层次来解决。
2004年7月6日至8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
机构间湄公河次区域打击拐卖人口项目及英国救助儿童会,在昆明举办五省预防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经验交流会,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公认,我国目前的打拐工作中存在许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缺乏一个清晰而完整的“长久之计”,反拐工作的战略重点出现偏颇:长期以来,反拐主要停留在事后的打击上,“一提到反拐,只知一味剿、剿、剿”,政府官员有一个错误的思维:宁愿花更多的冤枉钱来解决问题,也不愿把问题扼杀在萌芽之中。
专家们认为,这导致警方承担了过多的职责,用云南省公安厅的话来说,警方目前负重太过、苦不堪言,出现了公安一家单打独斗、公安内部又是刑侦一家唱“独角戏”的被动局面……”
警方苦不堪言到了什么程度?
在昆明,“百日会战”期间,迫于形势,警方给各派出所下达了一道死命令:辖区内再发生孩子失踪和被拐卖的案件,负责辖区的片警将一律下岗,所长免职;同时,实施案情“回报制度”,已经立案的案件,负责案件侦破的警察应该每天向失踪孩子的家长报告案情进展,如果群众提出意见,负责案件的警察也将受到下岗处分——昆明市公安局一位官员说,局领导也自知此举太过,“但没办法,来自上面和各方的压力太大,而且局领导也希望改变过去那种局面”。
此举在昆明民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一些了解警方难处的被拐孩子家长说,“我们很感激警方所作的姿态,但警察也是人……这样做我们以后也不好来报案了”。
贺平说,单纯打拐,结果却越打越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治病之道,“我觉得政府更应该像一个优秀的中医,整体看待病人,标本兼治”。
实际上,云南省公安厅自1999年始已对反拐及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反思,得出结论:反拐不是一个单一的打击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是一个维护儿童权利、涉及到“人权”维护的问题。警方因此萌发了改变现状的想法,当时云南公安厅刑侦总队高层已提出全社会参与、整体联动,变单一打击为预防为主、打击为辅的方向,并酝酿在社区建立预防拐卖的社会长效机制。
警方的观点跟一些社会群体和国际儿童权益组织不谋而合,早在多年前,他们就密切关注云南贩卖幼童的形势发展并着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1999年底,云南省公安厅与代表社会群众团体的省妇联、代表国际民间组织力量的英国救助儿童会联合在文山州广南县龙乜村启动了“多部门合作社区预防妇女儿童被拐卖”项目,尝试在农村社区将包括上至多个政府职能部门、下至每个村民的社会资源调动、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实现防止拐卖。
这一模式的具体实施是,组织成立一个多部门项目合作的机构网络,网络中的各部门都有一定的职责范围,公安负责治安管理,妇联负责唤醒妇女的权利意识以及维护孩子的权利意识,综合治理办公室则负责协调上层领导部门诸如政法委等等,将领导力量纳入网络;林业、农业负责在项目实施地的经济发展(拐卖发生的根源在于贫穷),以及争取政策和资源———龙乜在过去是又穷又不受重视,许多扶持政策得不到。
项目还对各级别的部门以及社区的居民特别是村民们进行了培训,让他们明白各自的社会责任,以及自身的权利。因此,项目是在一方面加强权力部门的资源整合,一方面高度发掘村民自治的潜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赵捷说,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项目,实施4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那些过去的人贩子、罪犯、违法者,现在转而成了妇女儿童权益的维护者。
这个基于中国国情和地区实际而设计、运作的、被称为龙乜模式的项目,因为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在五省会议上被介绍给国内外132名专家、学者,目前已成为国内外极好的行动性研究案例。
英国儿童救助会项目经理黄金霞透露,目前他们和云南省妇联、公安厅正致力于龙乜模式的完善,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政府对反拐工作的重视及全局性考虑——理想的状况是,在省综合治理办公室设置一个反拐领导小组作为长效机构,把反拐纳入社会治安的常规工作,纳入各级官员的考核指标,以根本改变过去“运动式”的局面。
在贺平摊开的地图上,云南省的38个村标上了小红旗:省妇联已联合云南省综合治理办公室、公安厅、司法厅等门,并向云南省政府提出专项申请,筹集资金,拟在这些拐卖重灾区推广龙乜模式。
当然,这一模式的可复制性和长期有效性,还需实际效果的检验。
“一定看好自己的小孩啊,不然走丢了会后悔死的。”李启方回忆说。
李启方当胸举着个自制的大牌子,上面贴着一张4岁儿子李升的照片,旁边是用黑笔写的寻人启事。在他身旁,是40多个同样装扮的父母,大多眼含泪水,手挽手站在一起。碰到有过来询问的,就给对方看自己孩子的照片。
他们都是外地来昆的打工者,都在昆明丢了小孩,为了找回自己的“心头肉”,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呼吁社会的关注。
这样的自助团体被称为“寻子联盟”,共有近400个失子家庭参与其中,分布在广东、福建、贵州、湖北、河南、天津、云南等地。
生计,与孩子
这些丢失孩子的打工者,以摆小百货、卖衣服、卖鸡鸭等为职业的小生意人居多,他们通常住在人员混杂、治安较差的“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一边为生计奔波,一边要照看孩子。
他们的孩子也就成为了人贩子拐卖的首选目标。李启方所住的昆明市北郊官渡区,作为昆明外来打工者聚集处,同时也是儿童丢失最多的地区。近几年,该地区已经丢失儿童200多名,占到昆明被拐儿童总数的70%,绝大多数为外地打工者的孩子。
然而,这些外来工家庭有时候感到孤立无援。许多家长踏上了依靠自己力量寻找失踪孩子的漫漫长路,尽管这路走得那样艰辛。
湖南怀化的戴先生,为找到自己5岁的儿子,半年来跑了十多个省市,从云南出发,经两广、福建,一路北上直到上海,“南边半个中国都走遍了”。前后发了500万份寻人启事,并给全国2786个县级公安局发了求助书,花了30多万元,“小孩看了很多,但都不是我的”。
类似的情形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失踪孩子的家庭,为找孩子这些家长“像个无头苍蝇,到处闯,可一点线索也没有”。许多人为找孩子花光了自己的“全部家底”。
“人多力量大”
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成规模的“寻子联盟”主要有三处:云南昆明的“寻子联盟”集合了178个失踪孩子的家庭,广东东莞的“寻子联盟”组织起87个失踪孩子的家庭,河南郑州的“寻子联盟”有10个失踪孩子的家庭参与。最初一般只有几个家长,后来人越来越多,逐渐发展壮大。他们在一起,互相提供各自掌握的消息,彼此安慰。
林舜明在丢孩子后,“天天买报纸,就看看哪里有丢孩子的”。有一次,报上称一个市场近两年陆续丢了七八个小孩。他们几人就去市场周围四处打听,看到墙上贴的一张寻人启事,就联系上了其他寻子者。
这次行动,使得东莞的“寻子联盟”又多了六家新成员。为了联系更多的家庭,他们甚至还实行了“分片包干制”,选出住在不同地方的几位代表,各自负责自己所在的区域,有的还通过报纸、网络,广泛联络外省的失子家庭。到年底,东莞“寻子联盟”就联系到全国各地近百个丢失孩子的家庭。
而东莞“寻子联盟”负责人林舜明同昆明“寻子联盟”负责人李启方的相遇更富戏剧性:2004年7月22日,李启方被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请去做了一期节目,在节目中李启方讲了自己的遭遇以及昆明“寻子联盟”的一些情况,并播放了当地电视台拍摄的他们在东风广场上的镜头。
“也就一两秒钟吧,我就看到了一个家长牌子上黑笔写着的电话号码”,林舜明回忆当时看电视的情景,他今天还能记得这个0871-4591×××的电话。
按照电话打过去,从那要了李启方的联系方式,“我们两家就联系上了”。
后来,林舜明还带李启方到自己家乡找过孩子,他讲了那次的经历:
“我家乡潮汕那边,‘传宗接代’的想法很流行。有些人家连续生了几个女的就是没男孩,会托人买个男孩子传递香火。这样一来,买孩子的就很多。
“我知道有个8岁男孩,卖到我家乡有4年了,现在还记得他家附近有火车经过,他爸爸是个卖猪肉的。
我把消息提供给大家,李启方告诉我,他家就住在火车站不远,基本情况差不多,就打算过来看看。当时我还有顾虑,但是一想,都是丢小孩的,能帮上的还要帮。他在学校门口等了一天,最后没等到。”
孩子虽然最后没有找到,但毕竟增加了人们的信心,“你能保证下一个就不是自己的?”一位湖北的家长这样说道。联盟里的家庭,更多的时候是在彼此鼓励,彼此温暖。“现在,在外面看见别人一家三口,心里就堵的慌”,深圳的一位家长说,“我们这些不幸人聚在一起,感觉要舒服点。”
他们经常碰头。地点近的,两三天碰一次面;远点的,就隔十天八天去一下。路上打车,都是“抢着付钱”。到谁家,正赶上吃饭,“没有菜,就一锅粥,也要给盛一碗”。电话互相打,“大家聊一聊,可能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可是心情会舒畅些。”
林舜明说的更明白,“同病相怜”。
他们还会有一些集体行动,督促政府相关部门,呼吁社会关注。如2004年11月27日,郑州“寻子联盟”的10名家长在郑州市二七广场打出横幅,上书“10名被拐孩子父母用心良苦,20万重金酬谢好心人”;2004年12月20日,东莞“寻子联盟”的30余位家长一同进京,向公安部、全国妇联反映情况。
“毛主席说的对嘛,人多力量大。”贾少令很认真地对记者说。
“一定还活着,一直找下去”
家长们的不懈努力似乎起到了一些作用。丢失孩子严重的地区的政府对这个问题开始给予重视,采取了一些专项行动。拐卖孩子的“重灾区”——云南昆明的警方在去年下半年展开了一项百日打拐行动,要求在百日内投入百名干警花费百万元解救百名儿童。郑州市则于2004年12月29日,召开“打拐”工作会议,郑州警方向全市公布10名儿童信息,警方刑事技术部门在原先失踪人员DNA数据库中增加失踪儿童数据库。并特批20万作为专项经费。随着警方打拐力度的加强,一些被拐儿童也陆续被解救回来,其中有一些是“寻子联盟”中的失踪孩子。
2005年1月5日,被拐两年的5岁儿童郑帅权成为郑州“寻子联盟”中找到的第一个孩子。2005年1月7日东莞“寻子联盟”负责人林舜明的孩子林杰涛也被当地警方在江西找到。
“我还是那个观点,你一个人,再多钱都没用,把人凑起来才有力量。”林舜明如今谈起自己组织起来的这个“寻子联盟”,很自信。他觉得自己能找回孩子,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公安局重视了,再加上自己提供的有用的线索,“案子不就破了”?如果没有人主动搞这些事情,比如联系失子家庭,接受媒体采访,去北京反映情况,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他表示其他的家长“还得这么做”,还得继续团结起来。
林舜明在送别记者时,满脸是笑,他说自己这半年来从没有笑得这么开心,“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早日找得到,大家都开心”。
然而,“寻子联盟”近300个失子家庭中真正找到孩子的还是少数,大多数的家长还在煎熬与等待中苦苦度日。
唐建勋的儿子唐小虎,2000年11月2日被人拐走,4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寻找,从未想过放弃,“只要国家公安机关出力的话,应该还是有一点希望的”。
过去喜欢逗孩子玩的老唐,现在最怕见别人家的孩子,“看了就伤心,就想自己的儿子,想我的小虎。”
说到这,这个一直很倔强的男人,眼里都是泪。咬了咬嘴唇,半天才说出一句来:“我就想,一定还活着,我就一直去找!” 作者: 曹勇马晖 2005年01月20日10:05 南方周末
延伸阅读:
- 荣治和(云南)07-26
- 祁晓美(云南)08-27
- 2013年9月20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公安局认10-25
- 2013年8月31日云南省红河泸西县交警大队认尸启事10-10
- 2013年8月16日云南省澄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尸启事10-06
- 徐州打拐后续:没有父母认领孩子 福利院也拒收09-23
网友评论
以下是对 [卖孩子就像卖白菜 云南贩童黑帮之恶下] 的评论,总共:0条评论
最新文章
推荐文章